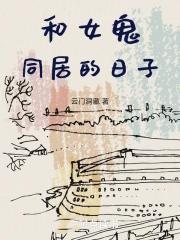一叶书库>九光当然不承认玩弄他 > 第48章(第1页)
第48章(第1页)
说完仿佛不够解气,奚落一句:“你可真会走路。”
此话过于刺耳,聂九光皱起眉头,见弥青始终一副逆来顺受的神态,她不得不喝止:“排风。”
她沉声训诫:“你怎么能说这么刻薄的话。”
聂排风不服气地还想争辩,可就算夜色昏暗他也看清了师叔异常不喜的神色,讪讪地闭上嘴。
他恼羞成怒地四处走动,抬头看见了挂在树桠上的萤火虫灯。转头看向师叔,他有心想撒个娇和解:“这个萤火虫灯真有意思,可以给我吗?”
出声的是聂排风,可聂九光在意的却是此地另一个人的心情。
刚才那声索要的话语仍在回响,这一刻她竟然产生一种负心感:“……还给弥青吧,萤火虫灯是他的东西。”
被拒绝了,聂排风十分委屈,孩子气地跺脚:“师叔,我以前想要什么你都会给我的!”
不等话语声停下,弥青吃力地大迈两步走到树桠前,解下布袋子,萤火虫四散着飞开,星星点点包围在他身边,又一团团飞走了。
聂排风目瞪口呆地张着嘴:“你——”
聂九光与弥青无声地对望。
她仿佛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要萤火虫们“解脱”,他也一样。
终于吐露爱意,弥青本以为自己的心灵能得到片刻安宁,然而随之而起的却是更强烈的不安和恐慌……她会接受吗?不、不要接受,有陷阱……期翼、忐忑、害怕、后悔等种种情绪在胸膛中杂糅,像无底洞一般,将他拉入没有尽头的深渊。
秋收后,弟子们都回到玄鸟峰,准备迎接一个寻常又温饱的冬天。
一天比一天冷了,某日聂神阙清晨起来打坐时,看见了树上挂着的寒霜。
不知为何她感到有些心慌,就算坐在道台上冥想,也无法平静下来。
晨练结束后,江傲来走进殿中向掌门禀报秋收的收成,起码这个冬天各个村子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惨事。
聂神阙沉吟,既然治下太平,那引起她心慌的事情就不是村民了。她思来想去,想到了“玄鸟翎”。她问:“你近日可有勤加修炼?玄鸟翎中的功法,可有一二感悟?”
江傲来低下头,语气惭愧:“弟子不才,虽然从未懈怠过修行,可玄鸟翎的法门始终无法悟到。”
聂神阙幽幽地叹口气:“为师倒也不是怪你。只是我今日心中突然有一种预感,她……要回来了。掐指一算你们师祖已经过世三年,玄鸟峰中再也无人修得玄鸟翎中的功法。到时她若回来,这里谁人能敌?”
江傲来面色凝重。他知道师傅口中的“她”是谁,她叛离玄鸟峰的时候,他已经懂事了。只不过家丑不可外扬,玄鸟峰的前辈们对此讳莫如深,如今知道“她”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就连聂九光都未必听过,因为那时聂九光才刚出生不久。
“她”如果回来,恐怕要引起一场浩劫。
告退后,江傲来打定主意,今日起必要专注修行,势要排除万难,领悟玄鸟翎中的功法。他是神族遗脉,天赋已是当世最高,就算玄鸟翎中的功法再怎么奥秘难解,如果连他都无法领悟,试问还有谁能?
同一日晚些时候,聂九光来向聂神阙请安。
聂神阙嘱咐女儿:“当前山下没什么琐事了,你要开始专心修炼。方才你大师兄江傲来在这儿跟我请示过,要研习玄鸟翎中的功法,你便跟他一块儿吧。唉,虽说近万年来天地间的灵力愈发薄弱,导致玄鸟翎中的功法越来越难以勘破,不过总要尽力一试。”
聂九光颔首表示明白,顿了顿,随即提起另一件事。
当听见女儿提起婚事时,聂神阙在此之前从未意料到:“谁?你的意中人是谁?”
她错愕不已,素来端庄的神态也有了些变化。
“弥青。”聂九光认真道:“他叫弥青,如今就住在药圃旁的杏林别院,仲夏时是我把气息奄奄的他带上玄鸟峰。”
闻言,聂神阙眼底的顾虑越积越深:“我不是指我不知道这个人……我的意思是,你们相识尚不足半年,你怎么会突然想跟他成亲?”
聂九光神情坚定:“我喜欢他,这跟认识了多久没有关系。他善良顽强,一片赤诚,就算只是凡人却勇敢地追寻所愿所想。当他内心苦苦挣扎着向我示爱时,他甚至明确地以为我不会答应他,可他还是不想违背本心,诉说了他的爱意,我怎能不为之动容?我愿意打破常规,破除修行者只跟修行者成亲的惯例,给他一个惊喜。”
聂神阙听着皱起眉头:“九光,你到底是爱这个人,还是被他的楚楚可怜打动?你分得清怜爱和喜爱吗?”
“当然分得清。”聂九光心中有数,反过来教诲母亲:“这世上有许多种爱,怜爱、敬爱、贪爱抑或纯粹的喜爱,并没有对错高下之分。我承认,我对他是由怜生爱,但这并不表明我的爱就不是爱。我爱他,我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
然而正是因为这份通透,才更让想阻拦的人无从下手。
聂神阙长久地没有说话。
半晌,聂神阙面露难色地反问:“九光,你打定主意要跟那个弥青成亲吗?你不会不知道,我一直希望,你跟你大师兄江傲来能结成良缘。”
聂九光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反感和抗拒:“母亲,我相信您也不会不知道,我对大师兄……从未生出过情愫!”
神情有些难以启齿,她本不想说得这么难看,可话已至此,她只好一鼓作气说下去:“您究竟为何要强人所难,在我看来您一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为何在此事上执着地逼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