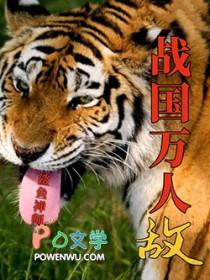一叶书库>家父儒圣,系统非逼我做粗鄙武夫 > 第32章 疑云重重(第2页)
第32章 疑云重重(第2页)
那恐怕牵扯到的东西就多了。
不过,曾安民看着那密密麻麻小字的卷宗,嘴角微微上扬。
他已经知道该怎么破案。
……
诏狱之中。
曾安民看着面前一脸惨白,躺在草堆之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犯人”面沉似水。
那人一袭囚衣乌漆嘛黑,身上散着浓浓的恶臭。
一动不动的躺在草堆之上。
只有胸膛微微的起伏还表明他没有死。
此人正是沈君。
能看得出来,没少受拷打。
悬镜司诏狱,进来便等于丢了半条命,这话绝不是虚言。
曾安民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身边的衙役。
他虽年幼,但身蕴浩然正气,举手投足之间已颇具威仪。
“把他放出来!”
“是。”
两个赤衣郎极为恭敬的打开牢门,如同丢死尸一般,将那年轻人从地上拉起。
“嘭!”
年轻人被扔在地上,任由惯性带起身体,整个身子都是软趴趴的。
这个时候曾安民才看清楚他的脸。
双目无神,浑身血乌,面容麻木。
“沈君!”
曾安民低头沉声对其淡道:
“本官乃新任左典吏,你杀婶一案,本官有意重审,你要如实招来,不得有半点容私!”
声音中气十足,颇有一种青天大老爷之相。
听到他的话,地上的沈君先是一顿,随后艰难的转目朝着一旁的曾安民看去。
曾安民面容沉静,与其对视。
他从沈君的眸中看到了很复杂的情绪。
麻木,坚韧,倔强……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行得正坐的端,婶婶不是我杀的。”
沈君这话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但每一个来查他的官员都会照例再对他用一遍刑具。
他也早已习惯。
“嗯。”
曾安民面无表情,坐在官吏给他搬来的椅子上,轻轻转动着大拇指上从老爹那顺来的玉扳指,良久之后,沉声问道:
“本官要问的便是那夜在灵堂之中,可是只有你婶婶一人?”
沈君听到这话,心里一沉,他脸上尽是苦涩。
每一个来问的官员都是先问的这话。
“是的。”
沈君回答的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