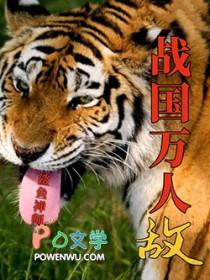一叶书库>元帅他总想谋反 > 第137章(第2页)
第137章(第2页)
那声音像是哑了一般,“雄主?”
粲澈嗤笑了声,“真会挑时间,苏元帅不是才刚离开不久吗?”
光脑没音了,粲澈全当那东西死机了,打开花洒,继续干自己没有干完的事情,“你最好有事。”
“想雄主算事吗?”
粲澈原本在擦头发的手一顿,“你是真的藏了书吧。”
毕竟木头人也有开窍的一天,确实让人稀奇纳闷的,一开始还以为是灵光一动,现在看起来倒是蛮有心机的。
“雄主同意了的。”
同意我追你。
苏竡明明知道光脑画面里只能看见洁白的天花板,却依然不肯错过一秒地盯着。
他能听到水花溅落的声音,伴随着粲澈像是带刺样的调笑,心里也像是潮水一般灌满了,他知道,即使回去,粲澈也不会跟他在一起,毕竟答应了那群小戏精。
但如果早点完成任务,或者任务的中途,总能讨点赏吧。
恍惚间又回到了他前往授封仪式的那时,名义上他已经有了元帅的权利和名誉,就差一个官方的授权。
那个时候,见到粲澈的时候,对方也是一如现在一般,带刺,像是在嬉笑,又像是藏着不满和另一种放纵。
为什么是放纵呢?
因为……如果不是放纵,粲澈根本不会接这个通讯。
苏竡沉了沉眸子,那声“苏元帅”像是轻易地将他拉到过往,又在深溺其中时被毫不留情地拉了出来,也是头一次知道,他深深地被吸引着,不仅仅是来自基因的迷恋,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法自拔。
带刺的金色玫瑰。
明明什么都干了,婚结了,事办了,还是不依不饶,像是期待着什么一样,却又骄傲地不肯给他指明路子,非要他自己去淌过,然后站在对岸,用一种复杂的目光,指指点点。
骄傲、矜贵,像是生来就应该被放在精美的橱窗里,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众生。
却偏偏喜欢去野地里肆意舒展枝叶,去追寻看不见的光亮,寻找另一种可能。
他在为反抗军奔波的那段日子,对方也在为雄虫探索一种可能,他们像是彼此对立,又像是在对方的眸中看到属于自己的影子。
苏竡将光脑死死地攥在手心,好似察觉不到疼意似的,其实他清楚,他早已经败了,败得一塌涂地。
雌虫在虫母压制下无力反抗,粲澈会带领这些雄虫奔赴前线,一切都会被改写,苏竡不怀疑粲澈带出来的雄虫的实力。
雄虫不会再像是牢笼里的金丝雀,但虫母之后,倘若帝国还在,雌虫又该如何呢?
他们反抗失败了,雄虫又逐渐强盛,可他们早已不甘继续卑躬屈膝,他这个首领,就会是那时的——所有雌虫最大的恶人。
老元帅的话好像还在耳边,“王——”
“我们要找到王。”
王是粲澈吧,他不确定,但不管是不是,他早已经在这样的裹挟中没有选择了。
光脑里响起了打开浴室门的声音,还有一些细碎的声响,苏竡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殿下。”
你会带着帝国走向一条……真的不再往复循环的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