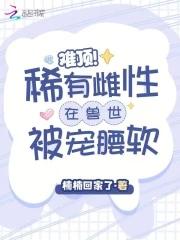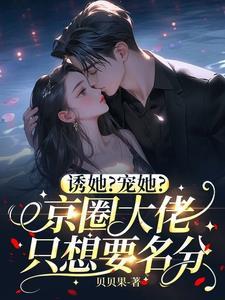一叶书库>大明:开局炸毁宁远城! > 第1章 天启五年(第2页)
第1章 天启五年(第2页)
而杜寒的父亲,身为明军夜不收成员,一家人跟随明军四处辗转,杜寒从呱呱坠地起就几乎没离开过军营。
作为一个军营长大的孩子,他的日常就是骑射捕鱼打猎,练就一身过硬本领,但对认字读书却是相当吃力。
天启元年,即杜寒十一岁那年,沈阳失守,他的母亲死于混乱中。
去年,杜寒的父亲也殉职于一次任务,至此,杜家唯一血脉杜寒成为新一代百户继承者。
理论上来说,这种已无实际控制区域的卫所本应停止世袭,但在当下用人之际,高层并未严格追究这些形式。
生活在辽东这片土地上的军户,由于长期接触建奴,许多人都是善骑射的优秀猎手,既通建奴语又知地形熟路。
这些人作为夜不收可谓再合适不过。
夜不收是当时非常特殊的群体,类似后世侦察部队中的尖刀分队。
他们深入敌阵探听虚实,任务范围涵盖搜集军事情报、执行刺探与破坏任务等。
任何琐碎的任务也都可能归入其中。
由于这类工作往往要在敌后活动,危险性极高的特点使得人员挑选异常苛刻,必须具备强健的身手和过人的胆识。
夜不收因处在前线与敌方接触的第一线上,常成为敌军重点捕杀目标,在辽东战场上被杀被俘的事例屡见不鲜。
为确保行动隐秘,通常一个夜不收小队不超过十人,同时为行动灵活也极少穿戴沉重铠甲。
因此遇到敌军时除非对手只是些零散的侦察部队,否则基本有去无回。
由于时刻面临死亡威胁,每次出发前夜不收们往往会与家人作生死离别,成功归来后亦要焚香烧纸庆祝大难不死。
当然,对手女真一方也建立了自己完备的情报网络,并设立专门对付明军夜不收的“捉生”
队伍。
对双方而言,消灭敌人侦查力量都属于当务之急,为此投入的努力往往不计成本。
就在昨日夜里,杜寒率领的夜不收小队遭遇了一支“捉生”
突袭,五个兄弟全部战死,杜寒被刀背击倒沦为俘虏。
抓活口以获取情报是“捉生”
主要目的之一,也正是因此杜寒才能暂保性命。
在那一记重击让他濒临昏迷的瞬间,来自现代的意识占据了他的身体,同时融入一些原主零碎的记忆信息。
恢复意识后,杜寒依然伏在马背上未动,双眼紧闭,身躯随着马的步伐轻轻摇晃,内心则默默寻找脱身之法。
多年的经验训练与生死边缘的反复挣扎,已让他养成了一种在危机中保持冷静的习惯。
心中不由暗暗叫苦:穿越就穿越吧,到了明代,成为类似夜不收这类先辈同行也算是缘分,但这以俘虏身份登场是什么道理?刚穿过来就要再送命一回?
仔细思量他与原主之间的一点共同之处,大概只有箭术了,这让杜寒心中略感安慰。
毕竟这门手艺对后来的人来说是种娱乐爱好,在这个时代可是一项保命绝技。
晨曦洒下,一群抓俘人有说有笑地策马而行,话语间夹杂着汉语、建奴话甚至蒙古语。
由于融合了原主的部分记忆,杜寒发现自己居然能够理解他们的对话。
从谈话内容里他辨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这是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建奴捉生小队,领头的是位红巴牙喇,另外还有两位来自汉军旗和两位来自蒙古旗。
尽管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但他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却毫无障碍,显然长期于辽东地区活动使得他们早已熟络无间。
要知道建奴捉生和明朝军队中的夜不收一样,都从各自的精锐军人当中挑选而出,担负的任务类型亦大致相仿。
约莫半个时辰后,杜寒隐约听到了流水声,侧目望去时只见一条宽阔河流横亘眼前。
他知道这是到达了辽河岸边,正式步入了建奴实际控制区域。
而这片水域,极有可能是自己脱困的最佳机会。
“前面就是驻扎站点了,在那里休整一会儿再去渡河。”
说话间,真奴举起手指向上游某个院落方向示意,并踢动战马缓缓向前奔去。
一名汉军旗下令之人吆喝一声,随手扯住了杜寒坐骑的缰绳将其带往前行。
其他小队成员也随之收敛嬉闹之声,迅速催促座骑跟随而去。
随着马匹起伏,杜寒暗自抬头打量那逐渐接近的目的地——一个建立于辽河岸边的军事站所。
依稀间他还回忆起初到这里进行侦察的场景。
队伍逼近军驿的时候,有几名守卫人员跑了出来,恭敬至极地打着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