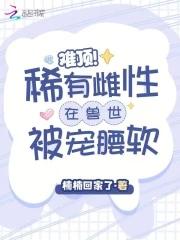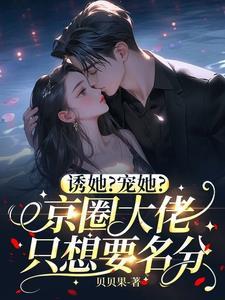一叶书库>大明:开局炸毁宁远城! > 第29章 夸大其词(第2页)
第29章 夸大其词(第2页)
所谓家仆兵并非真正的私人家奴,实则属于吃朝廷俸禄的正规军兵员。
然招募来源多样,多以将领私下招募为主,再辅以吸纳军中强者组成骨干部队。
因这些人为将领私下招募,效忠于招其入伍的将领,似主仆般忠心耿耿,长此以往故有“家仆”
之称。
自从明朝中期以来,无论是传统的卫所军户制,还是后期发展的镇戍营兵制,均暴露出重重问题。
拖延发放薪饷的现象导致军中哗变频仍,士兵逃亡问题屡禁不止。
虽军籍在册者号称上万,但大多为虚耗粮饷的疲弱残兵,仅凭他们勉强守城已是勉为其难,更休要说奔赴沙场奋勇杀敌。
这些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士兵,平日里根本无暇进行训练。
一旦爆发战事,即便官方临时大幅提升薪饷和奖赏,也难以激发其战斗力。
毕竟,没有基础能力的士兵,无论怎么激励都是徒劳。
因此,边疆将领往往会利用职权组建私人精锐部队。
他们亲自招募军事素质过硬的士兵,并给予丰厚待遇以提升忠诚度。
为了加强队伍的凝聚力,许多武将与这些精英战士之间通过认义父子等方式建立依附关系。
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利用军队中的空饷机制钻补替制度的空子以及清勾程序中的漏洞。
他们会冒充一些因各种原因(如隐匿、逃亡、疾病或死亡)已不在册的士兵名下的名额领取饷银,因为军籍上并未及时更新。
这种方式事实上被朝廷默认许可,名义上算是代表朝廷招募兵员,军饷同样由国库支出,将领并不需要动用自己的资金。
不过默认毕竟不同于明文规定,朝廷在某种程度上的默许下也会提高警惕,防止地方武官权势坐大,通常会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分化。
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控制私养家丁的数量规模。
所以这些边镇武将的家丁数量总体不多。
明清交替之时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名将,其实很多只是借助了自家私养的士兵才能取得战绩,而不是本人特别善战。
像戚继光这样的真正能独当一面的将军极少。
而把精兵交给各地守将并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在以文驭武的背景下,负责监督军务的地方官员运用起来难免存在掣肘。
于是,地方文官也开始着手组建直属自己的精锐团队——标兵营。
作为正统军备力量之一,标兵营可以优先获得优良资源如兵源、装备、粮饷支持。
所以在实力对比上,标兵营往往强于武将的私人部队。
像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这样的文官在其任内颇为倚重自身的标兵营。
其兵力从几千到几万不等,远超出一般武将所能掌控的家丁数目。
实际上,到了这个阶段,标兵营已经成为明朝末年军队中真正的主战部队。
即使如此,在部分将领手中,家丁体系仍被沿用。
毕竟标兵听命于指挥方的文臣,对于武将而言若想拥有一支额外的私人武装力量以增加自身威望与权力时,自己的家丁更为可靠。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家丁制逐步被正规军营兵体制所融合吸纳。
到了明朝后期,传统意义上单独存在的家丁系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规模化、正式化的军旅体系。
明朝晚期的军事制度混乱也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面对满洲人的战斗虽然并非完全没有胜算,但大型正面冲突中却鲜有获胜记录。
单就个体战斗力论及所谓“建奴凶猛”
只是部分夸大其词,实际上对方阵营内也有强弱划分。
然而每当涉及集团性作战、大规模阵地对抗超过一定人数时,明朝军队几乎无一例外陷入劣势。